

一句简素空灵,把明式家具的最高审美指向表达的淋漓尽致。体现简素空灵之美的家具被推为上乘之品,是有其艺术渊源和文化背景的,它直接受明清以来文人画的影响,两者在审美旨趣上一脉相通。从魏晋玄学开始,一直有着一个哲学命题:有和无。王弼在他的《论语释疑》中提出:“道者,无之称也,无不通也,无不由也,况之曰道。寂然无体,不可为象。”并认为“尽意莫若象,尽象莫若言”,这种意在言外、大象无形的哲学思维,对中国艺术精神影响至深。此后,南宋陆象山“心学”提出的外在世界“如镜中之花”的观点,直接影响了严羽的诗歌理论,严羽论述诗歌仿佛“空中之音,象中之色,水中之月,镜中之花”,突出了诗人主观世界的重要性,追求“羚羊挂角,无迹可求”的意趣。这种偏向于主观内心世界的艺术观,也为明代后期的艺术思潮乃至整个明清时代“性灵”派的出现埋下了伏笔。在明代晚期,从李卓吾的“童心”,到徐文长的“真我”、汤显祖的“气机”、袁宏道的“性灵”,无一不是讲究在人的内心发现人生与艺术的规律,对外在世界的描摩,即使是寥寥数笔,也要准确表现人生内心的情感和禅悟,所以,中国的艺术是人心灵性的表现,而不单单是技术性的再现,追求内心感悟与外在表现的统一,成为艺术精神中的一个核心理念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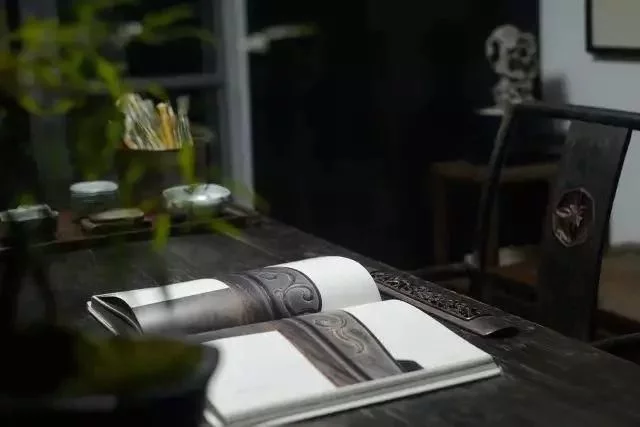
“空”是什么?是外像什么也没有,一片空白;“灵”是什么?是内心的充满和流动。在苏东坡的诗中,他谈到了动与静的统一、无与有的统一。在“空灵”的概念中,有与无的对立统一是最根本的,物与情、境与意、简与繁、少与多都是在有与无的对立统一基础上衍生而来。以前学作小品文,老先生要去首先学空,把小品文写得越空濛也就越灵动,其原因就在这里。但这种空,不是空洞、空白、空疏,而是巨大的充实。宗白华先生有一篇著名的论文《论文艺的空灵与充实》,探讨的就是这个问题。尽管他最后没有把两者完全统一起来综述,但他的根本意思是,与空灵相伴生的,是巨大的充实,在“空”中表达了“满”。







